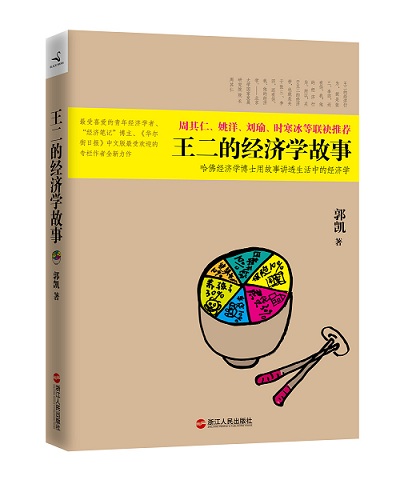
这是一本我花了不少功夫的书,不是什么传世名作,但却是一本我自己也会愿意买一本读一下的书。
《华尔街日报》今天发了一个删节版的后记,这里是完整版的,6000多字。
后记:王二的前世今生
王二是已故作家王小波笔下的一个名字。像我们这群70年代出生,90年代读大学的人,很多人都喜欢王小波的作品。因此,当我想为文章的主人公起一个名字的时候,王二是一跃到眼前最自然的选择。我的王二是一个没有脸谱的人物,至少我没有把王二脸谱化过。我最粗犷的想象过王二的样子是这样的:一个毫无特色的中年男人,头发也许开始有点变单薄,衣服毫不鲜明,身体微微发福……总之,一个不会给你留下任何印象的人。
你可能会好奇,我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写经济学?
首先,这就是当代经济学理解和描述世界的一种方式。理论,总是需要对现实进行抽象的。一个和现实一样复杂,无所不包,充满细节的理论就不是理论了,而是写实。在经济学里,王二这样的一个人用术语说就是“代表性主体”,整个经济就是由无穷多像王二这样的“代表性主体”组成的。如果你拿起一本入门级的经济学书,而这本书碰巧又是一个美国人写的,那在书里你很可能也会找到美国版的“王二”-王二的英文名通常会是罗宾逊·克鲁索。故事一般会这样开始:罗宾逊·克鲁索生活在一个荒岛上,罗宾逊的那一半是一个企业,他会雇克鲁索的那一半生产椰子果。生产出了椰子果之后,罗宾逊的那一半就会把椰子果拿到市场上去卖,然后给克鲁索的那一半发工资。克鲁索的那一半拿到工资之后,就跑到市场上买椰子果……
这恐怕是一个会让你觉得一头雾水的故事,是罗宾逊·克鲁索人格分裂吗?或者,你可能会觉得为什么只有椰子果,生产点别的不好吗,人不能只吃椰子过日子啊?但是,这就是经济学理解世界的方式。或者说,这是通过理论理解世界的方式:把所有不关心的东西全部抽象掉,把复杂的世界简化到一个模型里。罗宾逊·克鲁索的孤岛世界就是一个最简单的宏观经济,只有一个人罗宾逊·克鲁索,只有一种商品椰子果。但就是这样一个如此简单的世界,却包含了丰富的含义,工资和就业,生产和分配,厂商和消费者。这么说吧,在很多更为复杂的经济学模型里,浓缩到最后,你还是能找到罗宾逊·克鲁索的影子。
用“王二”写文章,就是我把经济学模型文字化的一个尝试。这个尝试是否成功,估计读者会更有发言权。主人公所以叫王二,而不叫罗宾逊·克鲁索,也意味着我主要谈论的还是中国的问题。在这本书收录的“王二”里,谈到了很多问题,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中国模式,房价,收入分配和公平等等,多是这两年在中国谈论的比较多的经济问题。王二虽然换了几十幅脸孔,但文章的模式却是千篇一律——前半段是王二的故事,后半段是讨论具体的经济问题,在多数时候王二的故事和后面的经济问题是一一对应的。
其次,这样写作和我写文章的目的是紧密相关的。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位到美国访问的拥有博士头衔的财经官员在华盛顿吃饭。席间,我们聊到了很多国内的经济问题。那位官员对很多问题见解很深,情况也很了解,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但当谈到了外汇储备时,他对整个外汇储备理解之错误,观点之外行,让我感到无限惊异。无独有偶的是,一位著名经济学家也在差不多的时候发表言论,他认为解决外汇储备过多的方式是把外汇储备分了―这是一个非常外行,但听起来又似乎合理的方案。
这些小事,再次证明了我的一个观察:在跳出了自己熟悉的领域之后,很多人都可能说很外行的话。这话当然同样适用于我本人。只是,中国和美国有一点非常不同。美国是个专业非常细分的社会,具体的问题都会有真正的专家出来解读,记者也会做足功课,保证报道里不会犯低级错误。我本人就接到过一些美国记者的电话,这些电话不是采访,只是求证某一具体关于中国经济的看法是不是合理或者帮助记者理解某一个经济现象,这样他可以顺藤摸瓜去找证据。因此,在美国具有误导性的言论是相对难出现在比较主流的媒体的。中国则不同。著名经济学家必然是要无所不知的,一些记者对制造标题的投入时常超过花在文章内容上的时间。所以,无知记者遇见外行专家的情况时有出现。
对于这样一种情况,写个上万字的八股文来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解释清楚在我看来是没有效果的,因为没有人会愿意读,读完之后可能更疑惑。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用最简单明了直观的方式,一针见血、一剑封喉地把道理说清楚。讲一个谁都能听懂的故事,突出事情的关键所在,就是我选择的一种方式。我是不是成功了,我无从知道。不过这是我的一个尝试。
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讲道理,不算什么写作上的创新,但对我个人而言,则完全是一个偶然事件。这事还要回到外汇储备的事情上。几年来,我写了不少关于外汇储备的文章,从中国的外汇储备还只有1万亿美元出头的时候就在写,写到现在3万多亿美元了还在写。老是写的原因是,看似简单的外汇储备,有时候能把一些经济学家都绕进去,而外汇储备的问题则随着储备的增多变得越来越重要。有一天,也许是有点无奈了,因为不管怎么写,我发现很多即使是愿意相信我的读者也实在想不清楚外汇储备,我于是写下了下面这篇《王二的粮食》(这里的版本略有删节,使得文章的形式和这本书的形式一致):
王二生活在一个荒岛上,自己开荒种地。每年打下粮食,一些留种子来年用,一些自己吃。开始每年打的粮食都不多,根本不存在剩余的问题。但后来有一年风调雨顺,多收了三五斗,除了放开肚子吃和留下足够的种子之外,还剩下不少余粮。很快夏天来了,剩下的粮食眼看就要坏掉,吃也吃不下,也没有多余的地可以播种了,请问王二该怎么办?
大概没什么办法,只能看着粮食烂掉。还能怎么办?也许可以酿酒、磨面或者做米饼,可惜王二都不会。
接下来,我们可以假设王二不是一个人生活在荒岛上,还有一个邻居罗宾逊。如果罗宾逊那里有块空地,王二可以把自己多余的粮食借给罗宾逊。罗宾逊把那些粮食当种子种下,等到秋天收了粮食,除了能把当初借的粮食还给王二之外,可能还多给一点,算是利息。这样王二和罗宾逊都划算,王二多余的粮食有了去处,罗宾逊的空地有了种子。到了秋天,王二和罗宾逊都能有更多的粮食可以消费。
这是一个没有货币的二人世界,这个世界里的硬通货就是粮食,王二在把粮食借给罗宾逊的那一刻,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王二有了自己的(外汇)储备。罗宾逊就有了自己的外债。储备也好,外债也好,都是用粮食计价的,货真价实,不存在“贬值”的问题。
但现在想象这样一种情形:罗宾逊那里其实根本没有空地,借给罗宾逊的粮食,他自己吃了也好,烂了也好,扔在海里也好,或者证券化了也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粮食从来没有被种下去。所以等到秋天收获粮食的时候,这个岛上的粮食并没有增加。罗宾逊也没有多余的粮食来还给王二。这个时候王二去找罗宾逊收账,罗宾逊能干什么?有三种可能:一、勒紧裤腰带还了;二、赖了;三、还一部分,赖一部分。
如果仔细想想中国的外汇储备,无论用什么货币储备,最本质的东西还是:中国人打下了“粮食”,借给了一些国家(比如说美国),这些国家没把那些“粮食”种了,而是吃了、烂了、证券化了,或者说“消费了”而没有进行“投资”。如果中国去要账,这些国家的选择和罗宾逊的一模一样:一、勒紧裤腰带还了;二、赖了;三、还一部分,赖一部分。
因此,如果这些国家采取的政策,不是使得最后的结果是“勒紧裤腰带还了”,那中国面对的结果只能是“赖了”或者“还一部分,赖一部分”,这和用什么货币进行储备没有直接的本质关系。美国至今为止采取的政策,还让人看不到勒紧裤腰带的特征,全部都赖了当然也不太可能,所以“还一部分,赖一部分”大概是必然的结果。
罗宾逊在借粮食的时候,可以给王二打各种白条,叫它美元也好,叫它特别提款权也好,只要罗宾逊没拿出真金白银的粮食,最后这些白条都是不值钱的。但如果真的需要罗宾逊能拿出粮食,那就必须得保证罗宾逊是把借来的粮食种了,而不是吃了、烂了或者证券化了。
话再说回来,假设罗宾逊执迷不改,于是王二决定不再把粮食借给罗宾逊。但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对付多余的粮食,那粮食最后还是会烂掉,王二还是要浪费粮食,只不过是烂在自己手上而不是烂在罗宾逊手上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浪费粮食的最终根源还是来自王二,因为他生产的能力超过了自己的消费能力,也就是经常提到的“内需不足”。
因此,如果不想再浪费粮食,看来王二真的是要学习酿酒、磨面、做米饼了——光会种地是不行的。
此文发出来之后,受到了意想不到的好评。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这篇文章说的东西没有争议或者是这一篇文章就把外汇储备的事情说清楚了,但这篇文章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启发,原来文章也是可以这么写的。
后来《华尔街日报》邀我每周在其中文网络上写一篇文章。刚开始我写了几篇文章,感觉不是太好,原因是找不到自己的定位。我不是记者,因此没法写新闻式的东西;我不在国内,因此不可能写得很贴近国内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我不是“著名经济学家”,因此不适合高屋建瓴地指点政策;我也不想装“假洋鬼子”,因此不愿意写那种简单的中美比较。而我又对浪费读者时间有一种天然的愧疚感。写点什么呢?用什么笔法写呢?这两个问题困扰了好几个星期。在一个周末开始动笔前,我想起了上面《王二的粮食》,我本能地觉得那可能会是一种可行的模式:针对国内的热点问题,用讲故事的方式,或是表述一个观点,或是澄清一种误解,或是提供一个思维的角度。于是就有了后来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上将近一年,每周一篇的“王二”专栏。这本书,主要就是由《华尔街日报》上已经发表的“王二”系列文章构成。当然,这本书里还有五篇从未发表过的“王二”,以及每个章节之前相对细致的导读。
话说回来,用王二讲故事不是没有弱点的,其实这里面问题多多。
我相信很多读者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我说的故事你觉得不对劲,因为我没有考虑A,B,C。我想说:你的感受是完全正确的。我不想假装我知道真理,事实是,我在多数时候并不知道。不要说面对如此复杂的中国,我自己的工作性质允许我到过世界上很多个国家,一些国家还没有中国的一个县大,人口还没有中国三五个小区加在一起的多。即便如此,有多少次,我还是会发现我所知道的理论和当地的实际有多不符合。“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此话时时刻刻都在我的脑子里。我希望自己说的是对的,但说错的时候,我也很坦然。觉得自己从来不会错的人,多半不是无知就是自大狂。
为了把一个道理变成一个故事,我有时不得不做的一个妥协就是,或者讲一个有点怪的故事,或者讲一个稍微有点扭的道理,否则故事和道理就对不上。这也许是因为我本人生活经验的贫乏,也有可能是没有花足时间,有时也是因为要说的道理比较复杂。总之,并不是每一个王二的故事都让我满意。只是,从我个人阅读的经验看,这样的妥协是很多作者都不得不面对的,这个世界有很多道理都是通过不恰当的比方来传授的。不要说社会科学,精确的自然科学也是如此。我读过一些介绍黑洞、弦论等高深物理的书。我在想,如果作者不会打比方,哪怕不恰当的比方,而只会写方程,那这样的书外行肯定是没法读的。
当然,讲故事的最大问题就是会给人这样一种误解:你可以随意编一个故事,来证明一个歪理。事实上,我也注意到一些有心的读者,模仿我的笔法,写了有趣的文字,但是讲了完全不同的道理。这就让我想起了一个有点恶心,但是非常著名的讽刺经济学家的笑话,这里是其中的一个版本:
两个经济学家甲和乙在路上散步。突然他们发现前面有一堆狗屎。经济学家甲突发奇想,指着那堆狗屎对乙说:你要是能把这堆狗屎吃掉,我口袋里的50万就归你。经济学家乙犹豫了一下,但还是鼓起勇气把狗屎吃掉了,得到了甲的50万。他们走了不一会儿,又发现了另一堆狗屎。这时乙对甲说:你把它吃了,这50万还你。甲毫不犹豫地把那堆狗屎吃了,得到了本属于自己的50万。在回家的路上乙若有所思地对甲说:刚才我们一共吃了两堆狗屎,可是我们谁也没得到什么。甲想了一下说:错了,我们创造了100万的GDP。
这是一个很尖锐的故事,可是,这是一个错误的故事。这个故事试图在说GDP是一个很误导的指标。在很大意义上,这个说法是成立的。只是,这个例子本身并没法证明这个观点,因为这个故事的两个主人公都属于变态:他们愿意支付50万来看别人痛苦。这个故事是首先有了两个荒谬的人,才有了后面荒谬的结果。或者换句话说,荒谬的结果是荒谬的人的结果。我们则是在用正常人的思维来看整件事情。如果我们思维也跟主人公那么奇怪,我们甚至未必会觉得这是一个笑话。
举这个例子的目的是说,并不是随意编一个故事就能说明一个道理的,哪怕结论是正确的都不行。故事,也得有前提,假设,逻辑和结论。我说的王二的故事,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有很清晰的经济学理论在背后支撑,这受益于我多年的经济学教育和从事经济学工作的积累。我不能肯定我说的都是正确的,因为即便正确的理论用在了错误的地方也会成为笑话,但是我可以保证的是,自己绝大多数的故事都是有理论支撑的。这么说吧,如果真的要像写学术论文那样给这本书加一个文献索引,这本书的文献索引会很长很长。
中国曾出不穷的经济问题,几乎可以让我把“王二”的故事无限期的写下去。我的这点自信是来自于我写博客的经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要写一篇博文,不是我的创造力无穷,而是中国可写的事情太多了,而写的人又太少。只是,写“王二”也是有成本的。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每个星期天的下午都变成了我的“写作文”时间。无论工作有多忙,在出差还是在家里,每周写一篇自己觉得能拿的出手,敢给人看的“作文”是铁打不动的任务。这也意味着,我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过完整的周末,有时候碰上出差,通常还要陪上半夜睡眠。随着工作生活变得愈加忙碌,特别是孩子方华的诞生,这种定期的写作开始由一种享受变成了一种负担。勉强维持,不是一种尊重读者的态度,当然更会有愧于《华尔街日报》这样一个大名鼎鼎的媒体。所以,我决定在王二这个专栏一周年之际,停止了这个专栏。
将“王二”的文章结集出版,是我写作过程中一直有的一个念头。因为有了一次出书的经历,我已经深刻的明白任何一本书的背后都包含了除了作者以外很多人的努力和心血,这本书自然也毫不例外。
我和《华尔街日报》的崔宇早在他供职于《新京报》时就认识,他本人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财经作者,整个“王二”的专栏一直是他在背后默默的策划和协调,我文章的初稿一般也都经由他修改再发表出来。《华尔街日报》的袁莉女士很有创造性的开创了“博客圈”的栏目,让专栏以博客的形式出现,既有灵活性也给了像我这样的作者一个发表见解的平台。《华尔街日报》的王莹女士和乔杕先生的细致工作让整本书的出版成为可能。
和我的第一本书《一沙一世界:郭凯经济学札记》一样,覃子洋女士和黄犀先生全程为我这个身在海外的人在国内出书打理了一切细节,从构思,到合同,到书稿的整理,从前到后事无巨细。
负责这本书出版的磨铁图书,不愧为国内民营书业之翘楚,为这本书的策划发行投入了巨大的专业力量。张庆丽女士细致入微地策划和协调了全书,刘杰辉、宋美艳、韩杨、魏玲以及他们的团队,为整本书的发行和市场营销进行了扎实和富有成效的工作。
众多的师友也一直关注和鼓励着我的写作和事业发展。我的老师姚洋教授欣然为这本书作序,周其仁教授,刘瑜老师,袁莉女士读了书的初稿,并很慷慨的为这本书写了推荐语。
我的父母对我的关心和无条件的爱,始终是我前进的动力,让我没有后顾之忧,让我无所畏惧。过去一年,最改变我人生的时刻是儿子方华的出世。孩子的第一声啼哭,第一个笑容,第一个牙齿,第一声含糊不清的“妈妈”“爸爸”都让初为人母人父的谷主和我无比的幸福。我们也在小心的呵护着这个幼小的生命,期望他能建康快乐的成长。在过去一年里,谷主和我度过了数不清的不眠之夜,而我还要把有限的空闲时间花在写文章上,谷主的辛苦和支持岂止言语能够表达。
所有的谢意,只能用这本书来还了。
郭凯
2011年10月12日于波托马克河畔家中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